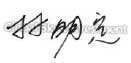進入6月,一位清大教授朋友轉來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執行長Jamie L. Vernon博士,他在NSF 正值75週年之際,對全球優秀科學家會員發出了一封信。
Jamie鼓勵成員們透過NSF 的社群媒體分享自己與 NSF 的故事,大聲疾呼強調聯邦研究投資的價值,敦促國會拒絕川普許多對研究有害的預算削減。
他呼籲,「所有的科學界與企業的研發人員都應該站在一起,共同促進對科學研究的投資,這是為保護美國三代人的創新提供動力的遺產……。」
前所未有的學術攻擊
世人皆知也相當驚愕,川普自第二任上任以來,對美國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攻擊。
2025年2月,川普簽署《學術改革與美國優先法案》,授權教育部、國土安全部和國稅局對大學進行全面審查,項目包括多元公平包容(DEI)政策、親巴勒斯坦抗議,以及與中國的學術合作等等。
學術聲望崇高的哈佛大學因為開放、自由派的傾向,首當其衝。2025年4月,教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凍結哈佛26.5億美元(約793億新臺幣)的聯邦研究補助,占其研究預算的40%。導致這些資金支持的1,200多個項目,包括肺結核、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和癌症研究等,因為資金斷裂被迫中止,至少15個實驗室關閉,200名研究人員失業,不僅影響300多名患者,數年來研究的成果可能付諸流水。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HU)的全球衛生附屬機構(JHPIEGO),因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 8億美元(約264億新臺幣)補助被削減,JHPIEGO在非洲和南亞12個國家的愛滋病、瘧疾和結核病防治項目,被迫縮減或終止。
哥倫比亞大學400多項生物醫學研究項目被終止,其中一項已經耗資2.5億美元、追蹤1,700人25年的糖尿病與老年痴呆研究,因資金凍結而中止,數十年累積的數據將面臨報廢。
普林斯頓大學也失去1.2億美元NSF補助,量子計算實驗室裁員30%,與IBM的合作項目延遲……。
自戀的秀場?
儘管也有不少輿論指出,過去數十年來,美國一些一流大學教育本質發生了改變,因為重商業交易而淪為權貴弟子的特權,或過於崇尚自由,成為許多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滲透的溫床,危及到美國國家自身的利益與安全。
網路一則流傳的訪問影片,探討了哈佛大學歷經350年的發展後,已經從知識殿堂變成自戀的秀場,逐漸失落了當初辦校精神和校訓宗旨。
2024年4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反猶太主義運動期間(註: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因抗議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而發起的運動,被指控有反猶太主義色彩,美國境內也持續出現反以色列抗議浪潮),美國國安單位確實也掌握到一些一流大學發展的高科技被中國人偷竊。
6月初,美國檢察官正式起訴了2名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指控他們將可摧毀農作物的有毒真菌走私到美國。根據聯邦調查局(FBI)向底特律法院遞交的文件指出,這種「禾穀鐮刀菌」會使小麥、大麥、玉米與稻米染上「赤黴病」(Head Blight),還可能導致人類和家畜嘔吐、肝損傷和生殖缺陷,這種真菌每年在全球造成數十億美元經濟損失,被學術期刊稱之為「潛在的農業恐怖主義武器」。
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但無論如何,川普這一連串以「保護美國價值觀」、「美國優先」之名的舉措,仍掩蓋不了粗暴政治對學術自由的干預和對知識創新的扼殺。
歷史上,政治與學術研究間的衝突與鬥爭屢見不鮮,也都涉及政治權力對學術自由和意識形態的對抗。
早在17世紀,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因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挑戰了當權天主教會支持的「地心說」,伽利略在1633年被公然審判,不只被迫公開否認日心說,還被軟禁終生。
1930-1940年代,德國納粹政權上台後,打壓一切不符合納粹意識形態的研究,愛因斯坦等猶太裔科學家的「猶太科學」,遭到禁止。
1950年代的冷戰期間,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發起反共運動,懷疑學術界存在共產主義滲透,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自由受到嚴重威脅。
1966~1976年,中國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為清除「資產階級」思想,被稱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成為主要被打擊對象,中國學術界因此嚴重斷層。
20世紀中期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限制黑人接受高等教育,許多學者因為抗爭被監禁或流亡。
科學面臨政治威權的壓迫,都顯得極為脆弱和無助……。
進入21世紀後,隨著全球化、數位化,即使學術挑戰了既有權威,權力對知識的控制慾也沒有消減,但人類文明的進展,民主國家政治對學術的干預手段,為保留對學術的表面尊重,已從直接鎮壓轉向更隱性而複雜的形式出現。
川普這一場赤裸的「學術清洗」竟發生在世界民主典範的美國,不僅直接讓教育與研究成為政治集權的犧牲品,違背了美國憲法的精神,也恐將美國推向學術與經濟衰退的深淵。
川普此舉對美國長期利益的損失,以及後續學術各界如何起義自力救濟,很值得觀察和省思!
因為人類有史來,科學創新(科技、社會、經濟、藝術等)對民眾生活真正帶來本質上的影響和利益,往往遞延到一代之後,甚至綿長超過三代。
研究型大學更是一國經濟創新的引擎,在美國,其每年貢獻了約1.2兆美元,約占5.5%的GDP。
川普大刀闊斧從經費削減破壞了這一個生態,估計在三年內,因資金和人才的流失,導致AI和生技領域的新創數量將下降10~15%,損失高達700億美元的經濟產值,喪失新技術的優勢,也將中斷未來的創新鏈。
歷史終將記錄美國高等教育這一個黑暗的時刻,但後果,卻可能需要後人數十年來修復。
偏頗的意識型態阻礙科學創新
然而,在為美國學界嘆息的同時,這種意識形態驅動的干預或攻擊,其實,也充斥在臺灣的生技界裡。
今年5月,浩鼎董事會決議停止OBI-822專案研發及二期臨床試驗,一時之間,特別是一些原來對浩鼎就抱持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紛紛群起議論兮、抱憾兮、撻伐兮,讓場景頗有重回2016年浩鼎案的氛圍。
研究單位有朋友把收到的各文章轉來給我,並對其中一篇廣被轉載的知名人士言論和一篇對張念慈的報導,感到不解與遺憾:「浩鼎自2002年創立到現在籌資近150億,但真正花多少錢在發展OBI-822這個疫苗應該是容易查到的,但卻寫的OBI-822似乎是翁啟惠的發明並技轉給浩鼎,然後浩鼎花10年、150億證明OBI-822失敗……。」
「這是對科學非常嚴重的誤導!」他疾呼。
事實是,OBI-822是一種針對Globo-H的癌症疫苗,OBI-821是這疫苗的佐劑,兩者都是來自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Samuel Danishefsky 的發明,先是技轉給美國Optimer,Danishefsky也因此成為Optimer創辦人之一。
該癌症疫苗所針對的標的Globo-H, 則是Harkomori 教授在1983年自人體乳癌細胞MCF-7中發現的醣脂類。後來,Optimer在臺灣成立子公司浩鼎,並繼續發展這個癌症疫苗。
但浩鼎量產此疫苗的過程中遇到放大生產問題,因此,浩鼎又從在San Diego的Optimer技轉翁啟惠的「一鍋式」醣分子合成技術,來解決該疫苗的醣分子生產問題,讓後續得以順利進臨床。
此外,OBI-822 沒有完成三期臨床試驗,也沒有解盲,是接受委員會建議,不繼續收案進行試驗而終止。但一些媒體依然直接以「三期解盲失利」下了結論。
「怎麼別人的疫苗不成功都是翁啟惠,況且任何新藥的臨床終止,也不代表一門科學的失敗,是不是用翁啟惠的名字就可以Bloody一點,新聞一定都要這樣嗎?」朋友很酸地問我。
或許從投資人角度看浩鼎的演變與起落,有其不同的切面解讀,但終止OBI-822專案事件,卻再次提醒我們,不基於理性與證據基礎的偏頗意識形態,只會阻礙對科學進展的認知,以及破壞創新的能力,而科學與創新正是社會發展的基石。
提到社會發展的基石,過完5月母親節,我要為讀者們特別推薦這期封面,我們副總編輯梓涵精心策劃的「臺灣生技10位女掌門人」,她們撐起了臺灣生技一片天,一片讓人一望是無盡舒展的藍天…….!